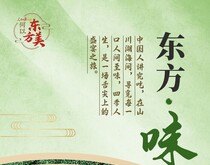经历十年酝酿,《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在3月9日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首次准确界定 “慈善”的定义,首次明确慈善组织公开信息的法律义务,并且首次把“慈善+金融”——慈善信托,提到法律层面,纳入到慈善事业发展的蓝图中。
降低公募门槛,做大做好慈善
基于慈善组织的准确定义,公募慈善组织不再局限在由政府发起成立的机构,登记满两年、运作规范的慈善组织即可申请公募权。基金会信息中心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3月9日,我国非公募慈善组织数达3313家,占我国基金会总数的68%。公募权的放开,结束了公益界“公家”独大的局面。

多次参与慈善法草案研讨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朱锡生在接受金台网采访时表示,公募权放开,意味着把所有的公益组织放在更加公平公正的同一平台上自由竞争,由市场来检验。对于一直有着公募权优势的机构来说,无疑面临着新的挑战。
另外,慈善法草案一次审议稿中因被质疑是对个人求助的一刀切而备受争议的“个人不可公开募捐”,该项在慈善法草案中得以修正。个人以及不具公募资格的组织结束了此前的“野生”窘境,只须依法与有公募权的慈善组织合作并接受管理即可开展公开募捐,募捐方式也确认了互联网募捐与线下募捐的合法性,大大拓宽了募捐渠道。
朱锡生认为,在公益互联网+时代,加之公募权放开,把选择权回归公众、回归市场,慈善行业竞争必然加大,所以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建设将愈发重要。“练好内功,不断增强组织的公信力,树立机构和项目的品牌就成为各公益组织的必修课和首要任务。”朱锡生说。
护航爱心,严惩贪、瞒、骗
仅仅在2015年,就发生了男子假扮知乎“女神”唱双簧骗捐15万、女子被自家狗咬伤谎称救人所伤而骗捐80万、父母为4岁重病女儿筹款结果挪用百万善款等等多起骗捐、贪捐事件。尽管负面事件一次又一次地打击爱心人士对慈善的信心,不过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近几年依旧发展迅速。每年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总量达到1000亿左右,每年帮助数亿人次,志愿者人数也超过了6000万。
不是每一个农夫遇到的都是蛇,但是每一颗爱心、每一次善行都迫切需要慈善法草案为底线严防死守。
作为我国慈善事业建设的第一部基础性和综合性的法律,准确界定了慈善的基本含义和行事法律准则,要求募捐方案详尽公布目的、时间地点、负责人资料、账户等,也首次明确对骗捐贪捐行为的定义和惩处。
慈善法草案第十五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分、挪用或者侵占慈善财产。” 违者将按照第一百零五条进行处罚,轻则警告、改正,重则吊销慈善登记证书,并对相关责任人处以刑罚及罚金。
假冒慈善骗取财产的个人或组织,则按照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由公安机关查处,构成犯罪的将入刑。
另外,超范围开展慈善活动、不公开信息或信息不真实、不发布年报、泄露助人者与求助者隐私、造假骗取税收优惠,这些行为都会触犯法律,慈善组织会被吊销资格,相关责任人将被追究刑责。
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政策与政府绩效评估研究中心主任王梅认为,慈善法草案提供制度保障、促进健康发展同时,增强了社会对慈善的信心,将推动慈善事业进入良性发展高速路。
慈善+,打造公益生命有机体
在公众认知里,慈善就是把募捐善款发给求助者,是零成本的“传递”行为。实际上,放眼国际,慈善机构租赁办公场所、人力成本、募捐活动、考查求助人员、运输慈善物资等行政成本通常占总支出的15%-20%。
捐赠只用于服务,而慈善机构是消耗型组织。将慈善组织打造成生命有机体,确保其生存,进而才能谈生长。慈善法草案描绘的创新战略蓝图中,慈善+金融的结合体——慈善信托正是顶层设计的亮点。
2015年年初,民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银监会,就慈善信托试点一事在深圳召开座谈会,鼓励深圳成为试点城市。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深圳市慈善会秘书长房涛对慈善+金融是体会颇深。
房涛表示,公益资本的构建应该借鉴更多的商业手法。公益资本蓬勃发展,才能支持慈善组织有更多的新方法、更大的能力去改变社会问题。
在实践的基础上,房涛认为慈善+金融除了利于公益界的自我生长,还有其现实意义。在公益资本用于公共服务时,慈善信托可以引导捐赠人在其专业领域上用商业智慧使得公益更有效率,与慈善一起共谋未来,真正去改变社会。
一日之寒难冻三尺冰。在采访过程中,多位慈善人士都表示,希望有更多的媒体界、金融界、企业界、社会服务领域的人士能够加入,共同促进公益新理念的普及和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的改变,帮助慈善事业的进化升级。
-
2024-02-20
-
2024-01-29
-
2023-02-03
-
2023-01-16
-
2022-0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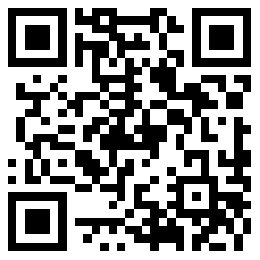



 热词科普
热词科普